
记者:我留意到您的英文版书名叫《云雀的眼泪》,而不是中文版书名《魔都云雀》,为什么?
贝拉:云雀的眼泪是因为她告别了故乡。云雀总在离去的空中一路流泪,在归途时会雀跃歌唱。日复一日不匆忙不懈怠,与时光共舞,与岁月缠绵。
记者:我看了一些摘选发现您是以第三视角来叙述与自己相关的上海故事。云雀既是作家的你,又仿佛代表着书中你,还隐喻为某种意向。可以理解为你的自传系列故事吗?
贝拉:打破惯常的第一人称视角,是刻意与自己保持时空的距离,更冷静、理智而客观地记载百年上海的家族故事。当我来到加拿大某个岛上,感觉一下子世界安静下来了,扑面而来的回忆像风一样……走到今天,我完全具有了梭罗“瓦尔登湖”那份回归自然、极简主义、精神超然与对人类的反思;也不乏对卢梭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论的高度认可,其“忏悔录”中的勇气与救赎,倾其思想,坦露着一颗透明的灵魂来书写他过往人生里的坎坷跌宕历程,这样的创作激情在已离群索居的我身上洋溢与澎湃。回归自然、崇尚自我、张扬情感的思想席卷了我的生命。我远离了繁华,进入了前所未有厚积薄发的井喷期。不为向众生倾囊我的高尚或卑微;只为自己的生命吹响信仰的号角。很难定义是不是自传,普遍认为对作家而言,写自传总是在晚年,而且往往都是在功成名就,所有荣耀与痛苦已成过去的时候。我还年轻(至少心理年龄停留在青春期);也尚未成功,而且荣耀与孤独都还在前方等着我,所以,确切说是用文学语言讲与自己有关的故事更合适。有些事年代久远,很多长辈也已离开,要再现百年家族史,容我在尊重客观前提下,展开想象的翅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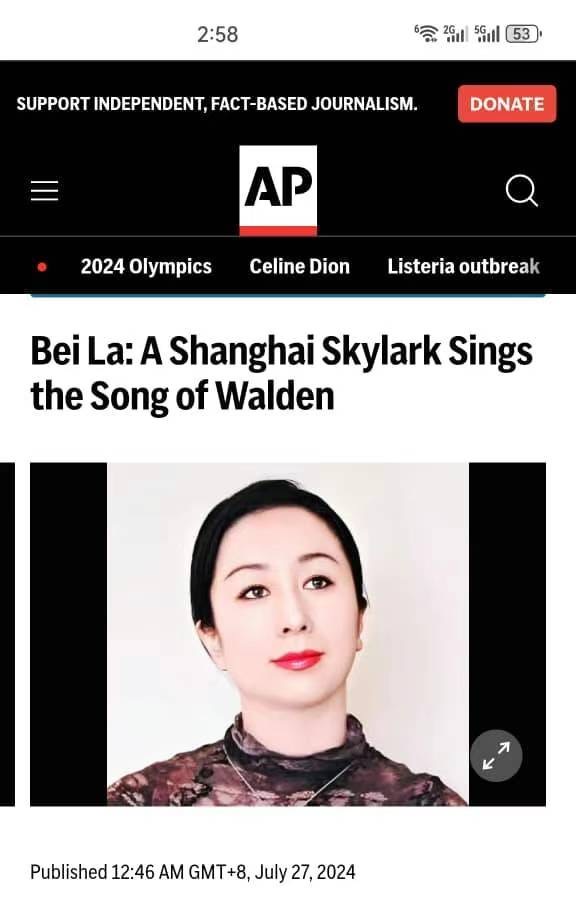
记者:迄今写了多少字数?与过去相比,文学特质有些什么变化?
贝拉:这个系列已经完成了四五十万字了。可以构成两部书稿。中文取名《魔都云雀》与《当云雀嫁给笨鸟》。文学上的表述改变很大。直接、简洁、幽默、自嘲、深刻、直抵灵魂。经历多了再不可能像年轻女孩那会儿空洞抒情了。
记者:为什么叫云雀?
贝拉:比较符合我的阳光性格。云雀被认为是吉祥的鸟,她的叫声可以驱走邪恶和不祥之气,因此被赋予了保护与庇护的象征。我身上的母性满怀。此外,云雀的悠扬歌声和优雅飞翔总在晴空之下,代表着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希望之鸟。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从上海奢华生活中挣脱出来逃亡加拿大孤岛的?
贝拉:不是逃亡,是回家。毕竟上海只是我的故乡,我年少就离开了。在上海世博会前后,我被魔都的繁华所吸引,来来回回、陆陆续续住了好多年。但是当这场全世界的疫情阻碍了飞行,改变了时代,变迁了世界。我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归属以及终将去往哪里这些终极的神学命题。我见证了魔都缤纷绚丽的时代,那真是人间的天堂啊!但在物质世界人们很难找到真正的自由与快乐,在大多数人纷纷涌向金钱与物质的深海时我选择远离魔都,只为内心丰富与宁静。因为瓦尔登湖一直在我的生命里泛起了涟漪。当大自然的美景如画卷般在我眼前徐徐展开时,我像孩子们欣喜与哭泣。所以说是文学唤醒了我,大自然召唤了我,上帝引领了我,让我奔赴我的“瓦尔登湖”。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牛羊成群结队是为壮胆,逃避某种宿命;而狮子往往形单影独,因为它足够强大。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哲学意蕴?
贝拉:是,隐喻了人学、哲学甚至神学。我见过强大的人都具有孤独的灵魂、他们特立独行勇敢无畏追求真理。像一头华丽的狮子王,充满威严与不可抗拒。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我在伦敦见到罗纳德哈伍德,也就是凭《钢琴师》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英国剧作家。他当时正在为我的小说《魔咒钢琴》改编电影剧本。很不幸他刚失去挚爱的妻子,情绪有些低落。我建议他去巴黎居住或换个新环境,暂时离开触景生情的家。但他说没事,守在家他的妻子就会来梦里与他相见。“最深的爱都是孤独的。”他说。他眼里闪着泪光却分明给我一种坚不可摧的爱的力量。望着他背影,你不会觉得他是近八旬的老人,而像一位经历过“霍乱时期爱情”,拥抱着“雾都孤儿”,指挥着“四重唱”,看见“蝴蝶飞出了潜水钟”,他却还在那里停留的英伦骑士。
记者:好感动。有时候伟大灵魂与懦弱的心之间的差别恰恰就是在遭遇一些磨难与苦难时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素质与勇气。是跟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吧?
贝拉:从成长环境到社会环境乃至坚定信仰都密不可分。更多还是被现实的功利性击败。很多人觉得我因为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几十年才成就内心勇敢强大。其实不是的,我有与生俱来的果敢。我七岁时我爸说我的生命里住着一位神话中的西方骑士。这说明我从小就在温柔的外表下包裹着可以引爆的内核。我是八月八日出生,是不是与我的星座狮子座也有关?(笑)
记者:瓦尔登湖意味着抛弃物质享受回到精神的宫殿,物质与精神对立吗?
贝拉:不能用对立与不对立来诠释。当你被物质的欲望驾驭,精神的追求就会丧失。但物质带给你的快乐是浅显的,至少对于我。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岛上生活,非常快乐。想吃鱼就开着游艇去钓鱼。每天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一天中主要时间用于思考与写作。听着音乐,灵感就来了,激情难抑,停也停不了。我真正远离了都市喧嚣,当暮色降临,我播放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光着脚丫子,在松软的草地上跳舞,用玫瑰花编织成花冠套在头上,俨然成了岛的主人。
记者:您被冠以浪漫主义作家果然名副其实。
贝拉:我总是忘却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我是谁?我究竟在世界上已经活了多少年?可以确定的是在探索真理之路上我首先找回了生命的意义;其次我在这个世界上还得活上几十年,我已知道该如何不虚度。
《魔都云雀》摘选
我不富有,但愿意像枣树一样慷慨散落我所有的果实;有天醒来我忽然发现,我的花园里已堆满了果子。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是因为我在黑夜里迷失了百年;将自己化为一泓泉是因为我在荒漠里已跋涉了千年。在富贵与成功者面前我腰杆挺直气场强大;在贫困与苦难者跟前我总是弯腰屈膝满含泪水。
当我的铂金包遭隔离酒店保安用高浓度消毒水喷洒;当我用温水擦洗却抹不去那白花花时;我的不快乐只有十秒钟,刹那间我领悟到是来自神的旨意,于是,我毫无犹豫地将它扔了并从此向所有奢华的物质生活作了断舍离。
若没有青春时代在日本的经历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接受多元文化浸染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将自己变成川端康成笔下的女子。烈焰与柔情交融;外在可爱内心坚强;风花雪月与终生守望。女人的爱魂才是日本文学的精粹。
这双肉嘟嘟的魔手有力记载了悲欣离合的命运沉浮。喜剧里泛着悲情之泪,悲剧中点燃希望之光,人生剧情恣意反转,思想更如脱缰野马,真理之光洒落在她眼中,她闻到草的清香、自由的味道以及自己灵魂的芬芳。她比任何时候都美……”
“其实每个人都能从某种或某些动物与植物中找到自己的特性与通性。比起云雀我更像一只雨燕,只要活着就不会停止飞行;比起任何一种花我更愿成为一棵草,不争不抢,在哪儿都能生长。太阳是我的母亲,月光是我的爱人,风雨是我的旅程。”
人被称为高级动物,体现在众生应是精神丰富而非追名逐利,因为高级与物质无关;在我看来,能与哀伤者同哀,与喜乐者同喜,具有一颗怜悯人类苦难的心才是真正的高级。
璀璨的灯火照在一艘艘夜行的游船,如一条狭长闪烁着点点光影的绸带,向着望不见边际的两端延伸……她依然在寻找那个女孩,但女孩却不知去了哪里。对岸若明若暗的灯火仿佛使她回到那些温暖的时光,她想伸手去触摸,却感到无力。一种从未有过的离别感向她袭来,仿佛某些东西行将消失。一辆夜行的货运船从北往南的方向驶过时,她从落地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了她的父亲,他朝她走来,将她紧搂在怀……
多少年过去了,原以为父亲唱的那首《故乡的亲人》早已消失在她童年的天空里了,但有一天却在自己悲伤的心中突然发现了它,那一刻她热泪盈眶,那是一个上海飘雪的早上。
他的吻带有一种英国梨淡淡的甘美,霎时流遍了全身;她不敢动甚至不敢想,所有的感受都停留在唤起这一切奇妙快感的身体上……
(照片说明:照片全部引自美联社新闻图片)